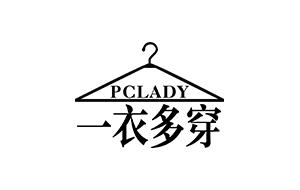2012-09-12 09:04 乐活人物
“江湖不问津”,高晓松手里的扇子上写着这几个字。看起来像是精心挑选过的,但其实不过是他从街边小铺顺手买的,只花了两块钱。
“江湖”这两个字,对于挥别了 6 个月监狱生涯的高晓松来说,今天也许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“坐牢也有好处,看到了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的一些人,然后你就会觉得挺平衡的,出来混都要还嘛,我欠的我都还了,我就平衡了。”
18 年前,25 岁的高晓松因为《同桌的你》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一举成名,这个正在捣鼓拍电影搞广告的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辍学生,变成了当年最知名的音乐人。尽管那首《同桌的你》直到现在不过给他带来了万元左右的收入,但这个“音乐人”标签贴在他身上 18 年,带给他除了姑娘之外无数的东西。
年少成名,少年轻狂。如今很多东西在高晓松身上已经看不到,尽管他一样能侃,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的神态,但很多东西已经渐渐消磨在时光中。2011 年,蹲在北京东城监狱里,他写了一封长信给1988 年那个写歌的高晓松,和他说一说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往事。
8 月 17 日,他抽着烟,摇着扇子,坐在我面前又陷入对过去的回忆,关于年少轻狂和中年受挫。他总算“老到可以谈谈未来”,也毫无顾忌地说起过去。
“你喜欢 1988 年的高晓松,还是今天这个自认活明白了的高晓松?”
“我喜欢 1988 年除了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,那个时代,那是一个好时代,但我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。我喜欢现在的我,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坏时代,我不是说中国,是全世界,美国也一样,非常沦丧,我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”。
“好孩子”高晓松现在北京的家里,住着太太、母亲、丈母娘、老丈人、小姨子等一大家子人,甚至他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把这一群人带来,跟着他走。这是中国家庭中最棘手的伦理关系,他却应对得很好,全家人相处得更和气。他说自己开始眷恋家庭生活,眷恋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日子。
B :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开音乐作品会?是觉得终于可以老到和老朋友们一起站在舞台上去怀旧了么?
G :其实去看的人也是怀旧的心境。我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事儿,都是被动等着,因为我 1996 年开了一场音乐会很成功,所以每年就有人来找。但我一直有两个不愿意,一是因为没有新作品,还开什么呢?今年正好有了这张《万物生长》,然后就可以开了;第二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卖人品求大家,这么多人都为了你聚在一起,你也不能让人白给你唱,所以你要攒人品攒很久,攒到我已经入行 18 年,服务了三代歌手,你在行业里也到了这个位置。你们都唱着我的歌去演出赚了那么多钱,然后我还没版税,我还得靠着当评委挣奶粉钱。所以我才开口说,大家一起来搞一搞吧,这个时候就瓜熟蒂落了。
B :那你有打算把它弄成一个长期的项目吗?
G :这一轮演个一两年,演个 32 场。现在 32 场都成了一目标了,大家都必须得开到 32 场,我肯定能开到 32 场。
B :这几年发生在你身上太多事,结婚生子,酒驾入狱,工作上也有很多新的身份,当选秀节目的评委,在视频网站优酷做脱口秀节目《晓说》,还出书、拍电影、开音乐会,感觉闹腾得厉害,没有停歇过。
G :对,其实我一直想这么做。但关键是,我得一样一样玩。在我看来,前些年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美国,奋斗也好,学习也好,什么也好。我觉得这件事是最大的一件事,我希望我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去干,而不是去玩票。我去美国不是旅游,去瞎看看。所以我正经地移民,正经地工作,去体会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的智慧,我特别全心全意地在干这个事。结婚生孩子也是一大事,不能新婚燕尔就忙得和孙子似的,大家好好在一起待几年嘛。这两件事花了我 6 年的时间。我觉得这 6 年完全没有荒废,你虽然没干什么这儿的人眼睛里能看到的事,但你把自己彻底地改变了,你成了一个比以前辽阔很多的人,你成了一个快要活明白的人,你成了一个对东西方的很多东西有思考的人,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值得的。所以从美国回来之后,突然什么都来了,其实我也不想用厚积薄发这个词,就是突然通了。通了以后你干什么事都会游刃有余,会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B :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高晓松看起来变化很大,以前很多人都觉得你是特别傲的一个人,年少成名,出身不错,带着那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。但你开始总说一些“很感激”、“很感恩”之类的话,这种心态是怎么转变过来的?是和酒驾这个事有关还是到这个年纪了?
G :我觉得可能都有吧。到这个年纪了这很重要,不然到这时候你还没活明白就很惨。年轻人就应该狂傲,你别像老头那样,有什么意思呢?我觉得这跟在美国做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关系,因为你在那儿,谁都不知道你是干嘛的。我在这儿少年成名,在行业里一直都在第一线,跑美国去就是一五流的小导演小作曲,琴弹得还没人家卖琴的弹得好。我去买把琴,人家卖琴的比我弹得好太多了。他只挣 3 块钱一小时,低于加州法律规定的 8 块钱,因为弹得好的人太多了。你又不住在富人区。我住在洛杉矶,他们没人相信我在中国是著名的音乐家,因为在他们那儿,你只要写过一首歌进过排行榜前 40 名,你就可以退休了。那至少是 3000 万美金的版税,我没有钱住在富人区里。我在美国的制片人,他说:“你是著名音乐人啊?我不信。你看我住的这区多好,你看我 200 万美金这房子,我拍过那么多电影都不算我赚的钱,我只写过半首歌,就我一电影主题歌的歌词我不满意,我就自己填了个词。就那么半首歌的版税,买了这套 200 万美金的房子。”洛杉矶房价远低于北京,200 万美金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房子了。没人相信我写过畅销歌。
B :《同桌的你》为你赚了多少钱?
G :第一笔是 800 块钱。后来陆陆续续乱七八糟的加起来可能有一万块钱。
B :刚去美国的时候,心理落差应该很大,很难接受吧?你在中国本来自我感觉这么好。
G :是的,接受不了。你约任何一个人都得等一个半月以后,没有人重视你,而且你只能发邮件,打电话人家都嫌烦,然后不停地发了 4 次邮件总算给了你一个时间——午饭后到上班之间的 10 分钟。我以前还会和人家说“老子在中国都如何如何的”,结果人家都那表情,意思是你牛你怎么不住在富人区啊。美国只有两个地方最势利,华尔街和好莱坞。其他地儿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这个事儿,但好莱坞是极其在意的,所以刚开始一年多时间里才慢慢开始平和下来,自己重新学习《圣经》,学习人家中学课本。
B :学《圣经》?为什么?
G :所有制片人一听我的故事就会说:“你这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的故事,你太不了解美国了,虽然你英文说得不错,但是没用,你不了解美国人民。”美国人都有一特点,就是读《圣经》长大的,每个人都说:“我告诉你,你先去把《圣经》读一遍。好莱坞的所有故事都是《圣经》故事,只是披了不同的现代的外衣,所以你这故事一听就是你没看过《圣经》。”于是我就去学习《圣经》。后来他们给我一个严格的规定,就是讲任何一个故事的时候,你不能用“我”当主语,主语必须是观众,观众以为他是怎么样的,你必须这么讲故事。这就是他们那儿洗脑式的训练,必须每一句话的主语都是观众。你不能说“我觉得怎么怎么着”,你是个屁!凭什么你觉得这样?
B :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自尊不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?在摧毁之后又重建?
G :是啊,我讲的任何一个故事,人家第一句都会问你:“谁要看这电影?”一开始我还特别不服,还很傲,会回答说:“我会看这电影!”然后人家就会斜眼看着你,说:“那您去纽约吧,别在这混了。”所以慢慢地我这些狂傲的东西就都没有了,就会变得非常谦卑、非常察言观色。
B :为什么刚开始非要到好莱坞去混呢?
G :我想做商业电影,我不想再做独立小成本,而且我想学习他们的体系,包括这个国家的智慧。其实好莱坞的智慧就是美国的智慧,美国犹太人的智慧。虽然我后来只拍了两部电影,但也可以了。好莱坞特别势利,你要是一无是处,人家客气话都不对你说,一句客气话都不跟你聊,不会像中国人说:“你不错啊,但是我们再考虑考虑。”人家连这个都不说,人家说:“谁他妈看这电影啊?”特别不客气。后来聊多了,时间待长了,他们发现我历史很好,就开始对你客气点。
B :你是靠什么在好莱坞待下来的?
G :这个过程有点难,毕竟你刚去的时候,只带着两部小电影,以及一堆没人听过的歌,你其实是一个少数民族,混进一个大party 里。我到任何地方,人家大制片人只给你 5 分钟时间,讲故事只能说 5 分钟,如果写的话必须不多于一张纸,因为没人有空听你讲或是看。所以我都先和我家门口的酒保排练,先掐着表讲给酒保听,第一次巴拉巴拉讲了十多分钟,只好再来一遍。你在那儿低头做人这些年,你就已经磨掉很多棱角,再加上岁数也到了,有了孩子人身上的气息就柔软多了,狰狞的那些气息就少了很多。坐牢也有好处,看到了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的一些人,然后你就会觉得挺平衡的,出来混都要还嘛,我欠的我都还了,我就平衡了。你看到了你看不到的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层面的人,你看到了人家是怎么生活,所以我也没有怨天尤人什么的,我要再怨天尤人,那些被判 10 年、20 年的都不用活了。所以到今天,我就真正平和了很多。
B :你已经拿到绿卡,为什么迟迟不入美国籍?
G :我随时都可以入籍,但是我在犹豫。绿卡和国籍在美国就一个区别,不能选举或是被选举,除此之外,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也不可能被选举,我也对选举没什么兴趣,所以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入籍。
B :你对政治没有兴趣?
G :我对政治本身没兴趣,我只对政治背后那些生存的智慧有兴趣。比如国家的理想,待了这么多年,我发现美国是一个自由超越平等的国家,这和欧洲不一样,欧洲正好反过来,平等超越自由。而这些有意思的智慧都和文化有关,我只关心和文化有关的东西,因为不管你是写剧本还是什么,你做的就是文化,这些就是文化的一部分,至于具体的政治的那些事,我是一点儿都不关心。就像科恩兄弟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:“美国没有警察的时候,也不是人人都杀人。”科恩兄弟那句话极大地震撼了我。美国现在有 300 万警察,杀人的一个也没少。我特别崇敬科恩兄弟,他们也是犹太人,我在我的节目《犹太人》里面提到三个犹太导演:科恩兄弟、伍迪·艾伦和斯皮尔伯格,他们看问题极深刻。其实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者,可能我老了以后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,我觉得这样挺好。
B :按照你的自由主义性格,到现在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把你困住吗?比如婚姻?
G :我现在唯一的能感觉到的困扰是点菜没点好。因为我走遍世界,我特别五香嘴,精极了。偶尔会出现点菜失败了,我就会特别特别困扰,我会想:咋都活到这岁数了,竟然能把菜点失败了。除此之外没什么困扰。
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
B :宋柯开了个餐馆,你这么爱吃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开?
G :我到现在什么都没开过。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多,我还能当记者呢,我没准儿也能拍照片,我没准儿还能犯罪,我至少不会那么傻就让人给逮着了。能做很多事,但你不能都去做,我觉得凭我这么多年攒下的资源和人品,我也是可以做生意的,我就不做,我什么事都不做,因为我觉得没意思,我只干有意思的事儿。另外是我欲望特别弱。譬如说我想买房,那我就得想办法了,但我又不买房。
B :你不买房,全世界各地都在租房子住?
G :租房子很好啊,想住哪儿就住哪儿,今儿看到这个就住这儿了,明儿看到那个就住那儿了,无非就是倒霉两天,每次搬家的时候都说:唉,要不买个房子吧,都麻烦死了。我一想到买房的后果,我就想着不要买了,因为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。我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结构里,但是一买房会破坏,因为你需要很多钱,当你需要很多钱的时候,你就想做点什么事,你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,你就想利用别人,你一想利用别人,你的整个的稳定的生活结构就破坏了。
B :你书里说不买房是受了你妈妈的影响,她曾经跟你说“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。所以你们全家都是无房族么?
G :我妈也没买过房。我妹也没买过房。我妹钱比我多多了,捐了很多小学等等,但从来没买过房。我妹妹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,现在回来了,以极简的方式生活,吃素,德国籍的孩子送到民工小学上学。我老婆是很爱穿衣服的,我妹的所有衣服都是我老婆的,穿我老婆不爱穿的。我妹妹很疯狂的,她一个人可以骑着摩托车穿越非洲。
B :听起来你们全家都很洒脱,你觉得你做过什么疯狂或者让自己骄傲的事?
G :好像没有,对我来说一分钱不带去要饭那都不叫疯狂,这个事情我也做过,和家里人打赌,我想组乐队,他们不让,便想为难一下我。他们说你敢吗?你敢拿把琴就走吗?我说我敢,于是爸妈搜我身,把钱都搜光,给我买了张火车票去天津,说一礼拜后你再回来,如果你坚持下来,乐队的预算和资金立马就拨给你,因为组乐队要花很多钱。虽然我们家心疼我,只让我去了天津,爬也能爬回来,但真一分钱不带就上天津那也挺要命的。
B :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?后来打赌赢了么?
G :大一。我记得我在天桥那边弹琴,一天下来就要到了 5 毛钱。然后花了 4 毛 7 买了盒烟,一口饭都没吃,当时 1 毛 5 可以买一方便面了,但是我有很多感慨,我得买盒烟。第二天,我想可能大学会比较喜欢这种事,就去天津大学卖唱,结果被人举报了,被学校保卫处抓起来了,说我是流氓。最后是被我们家领回去的,导致打赌失败。但是我们家的教育是特别好的,特别西式,虽然我失败了,饿得半死,但回到家就看到一大桌菜。从那以后到现在,20 多年过去了,没有人提过这件事,包括那一天,也没人提什么你打赌失败了,因为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男的,你心里肯定都明白了,那还提它干吗?
B :那还蛮有趣的,在这种鼓励下,你应该会干出更多不靠谱的事。
G :我确实经常干这种一分钱没有就敢出门的事。我在欧洲也发生过这种事,浑身上下一分钱没有,卡也刷爆了,没存款,我从来就没有过存款。我买不了房子就是因为没存过钱。最后打电话给北京的哥们儿,说你先借我点钱买张机票,然后他给我订张机票,让我去国航在罗马的办事处去拿机票,于是我又蹭了各种车去了罗马,拿了机票。最后坐着免费的接驳车上了飞机,一看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。我高兴坏了,我就问他,你能借我点钱吗,回了中国到机场我就还你。他说行啊,然后我和他套近乎,因为人家借钱给我了,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呀?他说我是作曲的。我更高兴了,“你作曲的,你不认识我吗?”他说我不认识啊,我心里一下特别不高兴,作曲的居然还不认识我啊!然后我说我是高晓松,他说我没听说过,我气坏了,心想说出名字来都不认识,我就问他:“那您叫什么呀?”他说我叫瞿小松,我顿时消气了:“嗨,瞿老师啊,大师大师!我不算作曲的,我只是写歌的,您才是作曲的。”
B :我感觉你现在的状态特别自在,是不是把很多东西一点点放下来,就越来越自在了?
G :虽然我有很多毛病,但我从小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观念,这个观念到现在我都觉得一生有益:我从来不想自己要什么,我只想自己不要什么。我一直这么生活的,所以自在就是你把不要的东西都不要了,那就好了。
B :你怎么判断你自己不要了?
G :我一直都觉得,这东西只要我不喜欢,那就不要了。不管它是什么,只要不要了就不要了。
B :对你老婆来说,你这样的岂不是挺没安全感?她也不知道,万一你什么时候突然不想要家庭了怎么办?而且你又没有存款,又不买房。对于一个在中国式教育下长大的女人来讲,你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男人。
G :但是我到 40 岁了,我对这个婚姻,对这个家庭,我是越来越依赖。因为你已经过了你男性能量的成长期,其实你是在往后退,所以你会越来越珍视这些东西。包括乡愁,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就有了,包括孝顺,我以前也没有,因为他们太强了,所以感觉不到他们需要你孝顺,我现在也有了。我现在能跟妈妈、丈母娘都住在一起,丈母娘带着孩子跟着我跑,在美国大家都住在一起,回北京也是,丈母娘、老丈人、小姨子从我结婚起都跟我住在一起,共同生活很多年了。我还乐在其中,我原来是特别野的一独狼,看到我今天这样,我的那些朋友都傻了,徐静蕾说,你每顿饭都带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啊。我说对啊,我说我告诉你,我现在不但不再是那头独狼了,我现在家里人少了我还受不了。我觉得怎么没人了?不热闹了,没意思。
B :这么复杂的关系,一大家子人在一起,你们都一直很和谐吗?从来没有矛盾吗?
G :关键就是我脾气好,我只要脾气好,就都和谐了。你要是再有各种不平,那就完了。所以我说我是员外嘛,人家员外四房五房家里都能和谐相处,我这儿不就是俩老太太,一老婆,一孩子,还有什么不能的呢?老丈人关系也磨合得很好。
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
B :你做了这么多工作,拍电影写歌当主持人,为什么从来不考虑做个歌手?
G :我就是坚决不想做歌手,我从小特别狂傲地长大,然后我觉得做歌手、做艺人在台上冲大家说“后面的观众你们好吗?”我觉得这样不好,我们家也接受不了,因为做幕后你就能成艺术家了,或者叫文艺工作者,于是就坚决不上台。等到后来呢,我觉得晚节不保也不好,别说年轻时候挺瘦的没上台,等老了弄一老胖子上去唱歌去了,算了还是坚持到底吧,宁可去做评委,就到现在都没唱。但我挺高兴偶尔能唱两个歌的,每场音乐会上我都会唱两个歌,《一叶知秋》和《恋恋风尘》。
B :你在台上的时候会不会回忆过去?当台上台下一起唱你过去写的那些作品的时候,你会有掉泪的冲动吗?
G :我站在台上当主持人串场的时候没有,因为我说的时候会尽量让大家笑,我也不是一个苦情的人,我说的时候都是逗乐的,我和这哥们儿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,这哥们儿这姐们儿怎么怎么。但我确实会掉泪,当我站在旁边看到万人齐唱,泪雨滂沱,那种场景连宋柯这种铁了心肠的都哭了,我真的特别感动: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,你曾经抚慰过这么多人的心灵。
B :所以就是因为这个,就算你以前做过很多不靠谱不要脸的事情,你都可以原谅自己。
G :对。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原谅自己,一个人要是不能原谅自己,你就白成长了。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最后一定要能原谅自己。我现在就是原谅了自己,我连我自己都能原谅,我就能原谅所有人。总而言之,你总伤害过不少人,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,我曾经自私地生活过很多年,最终两件事会让你觉得特别平静:第一,你还了,该还的已经还了,你总要还,但是我觉得不同的还的方法,如果是以家人的寿命或是其他的代价去还,还不如去坐半年牢自己去还了挺好;再加上你原谅了自己和所有人,因为人生中不光是你觉得对不起别人,你还觉得很多人对不起你呢,包括家人等等,你还有好多讨厌的人呢,我现在都没有讨厌的人,我每次看到他们在微博打架我都兴奋不起来,要是过去我肯定直接就冲上去了,但我现在看着都觉得特别怪,为什么人们不能互相原谅呢?为什么就要这么难以理解?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理解。
B :你会更喜欢 1988 年的高晓松还是现在的高晓松?
G :我喜欢 1988 年除了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,那个时代,那是一个好时代,但我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。我喜欢现在的我,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坏时代,我不是说中国,是全世界,美国也一样,非常沦丧,我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。